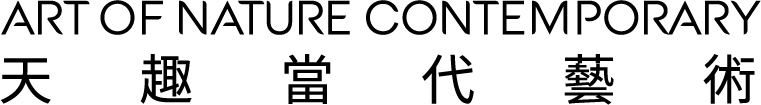
從此篇訪談中,我們將看到一位孤獨的求索者,為何及如何選定一條自己的道路,踽踽獨行。
相關文章
RELATED ARTICLES
相關展覽
RELATED EXHIBITIONS
徐晨陽是天趣簽約的重要藝術家之一,他以獨特的畫風,被北大美院院長彭鋒稱為“中國藝術界中尤為特殊的一位藝術家”。
本月底,徐晨陽的作品將在天趣「靈魂的肖似——肖像藝術展」中展出,本文將呈現徐晨陽於2018年的一篇長篇訪談,由於文章過長,我們將分為上下期。從此篇訪談中,我們將看到一位孤獨的求索者,為何及如何選定一條自己的道路,踽踽獨行。

對話藝術家/
徐晨陽,孤獨求索者與他夢境裡的星空(下)
Q-張榮東
本文轉載自《愛尚美術》雜誌《從寂寞雪國到夢境的星空——徐晨陽訪談錄》,內容有刪減。

徐晨陽,出生於無錫市,中國藝術研究院文學藝術院專職油畫家,美術學博士,國家一級美術師,研究生導師。2004年於日本東京獲第三十三屆《繪畫的現在—精銳選拔展》金獎,2017年於丹麥國家歷史博物館獲第六屆JC雅格布森肖像展二等獎。先後在國內外舉辦個人畫展26次。
1
“我不會畫一匹在草原上奔跑的馬,那不是我的繪畫。”
Q:我在網上也看了一些你的畫,你原來也曾經畫過女性和花的這種相互隱喻、相互映照的題材。在你的畫裡看到很多像徵、隱喻的東西。你雖然描繪一個物象,但是你指向的是物象背後隱藏的另一種東西,是一個畫面之外不可言說、不可表現的韻味、氣息或者指向,這導致你的繪畫不是單義的,而是多義的。
從繪畫風格上來講,按照古人的說法,你一定不是現實主義的,而是浪漫主義的,因為只有浪漫主義才用此物引出他物,而不是實指。當代中國像你這樣的經典圖式的繪畫多表現為現實主義,一個現實主義的畫家理解不了一個浪漫主義的畫家,這是兩條路。雖然指向的都是真和美,但是現實主義往往還是指向描述的對象本身,而你指向的是更為遙遠的遠方、更遙遠的世界。
徐晨陽:我一直是要與現實保持距離。我的繪畫與和任何可能影響我或者我可能會接近的目標保持距離,這是我創作最基本的姿態,因為我覺得藝術必須是獨特的。
既然是從事藝術創作,就應該提供一個獨特的、個人的、新的形式和體驗,和任何會影響到這種獨特性的因素保持距離,就算它可能是個捷徑,或者會讓我取得更好的效果,我仍然會保持距離。

《水星》,145.5 × 112 cm,布面油畫, 2015
Q:自從照相術出現以來,過去經典繪畫的很大一部分內容已經被取代了。你面對一個物象的時候,照相術可以更精確地保留、呈現它。那麼藝術存在、繪畫還有什麼意義?當畫家的作品失去了心靈的建構、失去了心靈的想像,那不就是一個毫無意義的圖形嗎?
徐晨陽:我在看到很好的風景時,從來沒有要把它描繪下來的衝動。我覺得這個地方好看,色調很好,構成很好,我可能欣賞它,但是從來沒有把它如實描繪下來的願望。
開始我也覺得自己挺奇怪的,後來我知道,我需要的不是對現實的再現,而是需要和現實保持距離。
所以我畫奔跑的馬,下面是雙色的格子而不是草原,我不會畫一匹在草原上奔跑的馬,那不是我的繪畫。

《御風之五》,73 x 112 cm,布面油畫,2017
當然我需要通過馬的這麼一種姿態來表達內心的一種意念。我不畫四蹄張開的馬,而是蓄勢待發的馬,後邊的風景都是圖式化的,每一張雖然都不一樣,但有一個統一的樣式,就是這種色調、這種格式、這種樣子。
我為什麼要這樣畫後面的背景?
第一,有了格子以後,就和現實拉開距離了,它就不是一匹現實中的馬,而是精神中的東西。

《枝》,145.5 × 97 cm,布面油畫,2015
第二,其實我要畫一個現實中的風景很簡單,但是我不要那樣,我需要的是一種圖式。打個比方,埃及的繪畫、浮雕,所有的造型都有統一的樣式,這就是一種程式化的藝術。
中國繪畫也是程式化的藝術,山怎麼畫、石頭怎麼畫、樹怎麼畫都有套路,這種程式化其實是藝術發展到很高的高度以後產生的,並不是不好的東西,低級的藝術不可能產生程式化的形式感。比如說你看到我這些畫,我希望呈現出一種程式化的風景,那些遠山、田野、樹林、道路,都是我心裡的一種風景。
在日本的時候,一個藝術雜誌採訪我,問我畫面中的背景有沒有什麼特殊的含義。我說會有一些寓意在裡面,比如說遠山和樹林,它是我對於祖先、家族這些概念的遐想。那些錯落的田野會讓我想到那些生生不息的生活。那些道路和溝壑,有著聯絡和溝通的意味。

《風景》,73 × 112 cm,布面油畫,2015
再比如說顏色,它也會有一些暗喻。
我們知道,在西方的宗教畫裡,顏色都具有一定意味,簡單地來說,紅色代表聖愛、生命,藍色代表真理,綠色象徵著生生不息、重生、不朽,白色表示純潔和完美,而紅色和白色一起用的時候,則被用來表示節日的歡樂等。
這裡面有色彩的暗示和聯想,我在運用色彩的時候也會考慮這些因素,當然不一定把它的這些含義講得非常明白,觀者可以去慢慢體會。

《節日1》,194 × 162 cm,布面油彩,2014
2
“直到那一天我畫這個男子,他就像一個宇宙一樣,他就是一個星球,他就是木星。”
Q:有時候像是夢境的疊加。
徐晨陽:也是我各種意念的疊加,這種風景一旦與現實的風景有了距離之後,精神層面的意味就會凸顯出來。
Q:我注意到你最近畫的舞者,這個男孩是你發現的模特兒,是吧?
徐晨陽:對。

《木星之二》,194 × 72.7cm,布面油畫,2015
Q:在其他訪談上我也看到大夥兒都在詢問這個問題。你看到他沉浸在自己的夢境或者白日夢裡,你看不見他的夢,但是你已經感覺到他進入到另一個世界,這樣的描述實際上糅合了你指向的一個不可言說的夢境,它不是實指的,他的姿態本身不是主要的,這是非常有意思的,是對畫者精神的探索,在一個形象裡面融合了一個冥想的世界。
徐晨陽:人物畫是我主要的創作題材,我之前畫一些女性,後來畫這個男子,我畫他,一定是他的形象,或者他的氣息觸動了我。
剛接觸這個男子時,他是北京現代芭蕾舞團的一名舞者,當時我看他的一個演出,一下子覺得可以畫他。我之前就想表現男性,只是一直沒有找到一個切入點,看到這個舞者後,感覺他可以進入我的畫面,於是就請他做我的模特。後來他去做了演員,前幾年崔健拍了一個片子《藍色骨頭》,他是主演。

《舞者12》,79 × 54.5 cm,紙本油畫棒,2012
當時我想畫他,與他的形體給我的感覺很有關係,恰到好處的流暢線條和肌肉,還有一種沉靜的氣息,這個很關鍵。同時,我希望模特最好是中性一點,不要有明確的傾向,這樣留給我表現的空間就大一些,便於注入我想表達的內容。
最終畫面上呈現出來的可能和他原型不太一樣,但是卻符合我需要的一個狀態。比如說舉著手的這麼一個姿態,這個姿態每個人都會做,但不是一個常規的姿態,這麼舉起來以後,就形成了一種儀式感,有一種意味在裡面,這種意味可能是宗教性的,也有人性方面的體現,既是伸展,又有掙扎或者被束縛的意味在裡面。一旦經過好多張的重複以後,它就會產生一種意義。

《舞者15》,79 × 54.5 cm,紙本油畫棒,2012
3
“我可以在畫面裡表現我的宇宙觀了”
Q:你的畫裡面,也有這種多重的空間、不同時光的聚合。
徐晨陽:是的,《記憶流星》系列都是多個畫面的組合。我們對比一下,《木星》系列是有主體的,表現的就是這個舉著手的男子或者說是一個木星,而《記憶流星》系列,一個畫面裡存在了多個景象,主體也不再是一個而是幾個且相互獨立,不再是表現一個主題,而是在營造一個空間了。
當然,最初的想法是記憶的碎片,以這種散亂的方式呈現著,這種畫面給觀者更大的空間,是觀者可以進入的一種繪畫。

《流星記憶之五》, 112 × 73 cm,布面油畫,2017
Q:木星這個點非常好,有一個非常宏闊的空間,我們也像宇宙茫茫星辰裡面的一個點,而你的畫也是由這個點累積而成的。
徐晨陽:去年5月份,我在北歐獲得了一個肖像獎,我後來知道這是一個很嚴肅的獎。
大概有十幾個國家博物館的館長作為評委,在一千多件作品裡面選出130張參展,再評一、二、三等獎各一名。當時有一個俄羅斯基金會的主席,一開始以為我的繪畫是點彩,後來發現不是,就讓我給他解釋一下。
我說,第一,這肯定不是點彩,這是我們東方的、中國的一種方式,是一種堆積的方法。中國文化傳承的方式是堆積,不斷的積累、豐富,而非西方的否定之否定;第二,我畫的是木星,這無數的點,就只有一條細細的線把形體區別開來,身體和背景如果沒有這根線,它就消散了。我們的人體、包括所有物質都是這樣。

《木星5》,162 × 117 cm,布面油畫,2015
Q:對,有凝結它的一個力。
徐晨陽:我從小就覺得那些微小的分子上面也許存在著一個宇宙呢,它也許就是太陽系,也許這裡面還有個地球,是那麼那麼地小,小到完全不能想像,從這個意義上看,我們可能就是非常非常巨大的。而我們這個銀河系則是更大宇宙中的一片塵埃,在其中的我們又是極其渺小的。
Q:你這個想法和中國傳統文化暗合,芥子中可見須彌。
徐晨陽:這個是我很樸素的一種體會,大概初中的時候就有這種意識,感覺我們所處的宇宙就是這樣的。我的這種宇宙觀一直存在著,但沒有找到合適的方式把它表現出來。直到那一天我畫這個男子,他就像一個宇宙一樣,他就是一個星球,他就是木星。這一下就串起來了,我可以在畫面裡表現我的宇宙觀了。

《木星3》,162 × 117 cm,布面油畫,2015
4
“都是我以自己的方式向東方的傳統、向唐宋文化的一種接近。”
Q:這個方向和你過去的繪畫相比,有了一個更深的可能解讀的範疇。
徐晨陽:我們剛剛講了,這種堆積的方式是東方式的,堆積使得顏料和顏料之間有了厚度和縱深度。其實這種縱向的顏料關係是東方式的、水墨的、滲透的東西,而點的聚散又牽涉到中國的道家思想。
Q:你對時間的這種探索和中國古人是一樣的,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包括時空,傳統中國畫把不同的時空凝結在一起,它是糅合無數的視角,最後形成了一個心靈印象。你和中國繪畫傳統離得非常近。
徐晨陽:裡面的光也好、影也好,時間也好、空間也好,它其實是一個沒有拘束的、沒有限制的一個時空形式。
在繪畫裡去接近中國傳統繪畫中的散點時空表現也是一個嘗試。在西方的繪畫裡面,那種空間、光影的時效性是很強的。

《流星之八》,112 × 73 cm,布面油畫,2018
Q:不知道你自己察覺沒有,你繪畫的色彩傾向也和中國傳統繪畫離得很近。
徐晨陽:應該是的。
Q:類似於赭石、石青、石綠的色彩特別多。
徐晨陽:它是分階段,我前幾年全部是暖色的,紅得很濃烈。當時有朋友來看了以後,覺得不大能接受,覺得怎麼那麼紅,但是後來發現我在紅紅的調子裡面會有很多變化的層次,慢慢大家就接受了,覺得也很好看,顏色與眾不同。
早前我有一個很偶然的發現,百度有一個圖片搜索功能,我用我的繪畫去搜索跟它相似的繪畫,出來的全部是歐洲的宗教壁畫,很暖很紅的畫面。這種色調上的相近,既是一種巧合,也是因為我的畫面中原本就含有崇高性、宗教性的表現需求,所以這種相近也就很自然了。
而從2017年開始一下子又變了,進入《記憶流星》系列的創作後變成這種青綠色彩。既然畫面上出現這種顏色,那麼這種顏色必定符合了我當下的某種心理需要。同時,我覺得這個系列的顏色有很大的表現可能性。畫面色調變了,構成也變了,這個顏色很東方。

《8春水-星辰之三》,162 × 112 cm,布面油畫,2018
Q:很東方。我們雜誌做青綠山水研究,沿著中國的石窟走一遍。石青、石綠是佛教壁畫的基本色,道教壁畫也是這樣。阿富汗的青金石色彩千年不變。就像你說的,那是來自大地的色彩,它不是人工化學合成的,而是從地下開采出來的天然礦物,把它研磨碎了,就是世界上最璀璨奪目的顏料,而且非常沉靜。像新疆克孜爾壁畫,千年過去還是神采奪目,它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這個顏料本身也意味著一種永恆、一種很神聖的永恆。
徐晨陽:我2018年1月份在中國美術館做了一個名為《記憶·流星》的個展。展廳展示的主要是我的《木星》系列和《記憶流星》系列。這兩個系列對比起來看還是很能說明問題的。
《木星》系列要早一點,畫面焦距於一個主體,有紅色的、宗教般的色彩處理,而《記憶流星》系列則是東方式的散點時空,背景色則接近中國傳統繪畫裡的石青、石綠。

《流星記憶之六》,112 × 73 cm ,布面油彩,2017
實際上西方的建築也強調主體性,比如他們的教堂,往往就是一個單獨的主體建築,而中國的建築強調的是一種空間概念,一種散點式的庭院格局。
所以可以說,我最近的創作,無論是色彩的改變,還是從主體到空間的轉換,都是我以自己的方式向東方的傳統、向唐宋文化的一種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