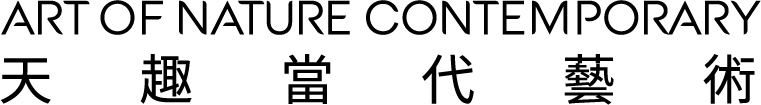
“在香港這個社會,能做幾件對得住自己,對得住香港人的作品,還是蠻好的。”
相關文章
RELATED ARTICLES
相關展覽
RELATED EXHIBITIONS

採訪&撰文 | 蘇曉Chloe
攝影 | 林秉韜BTO
策劃&審校 | 湯石香
1
入秋後的香港依然悶熱,穿過港島東的街市後,我們到達朱達誠老師工作室時已經汗意涔涔。
“你們來啦!”時年已79歲的朱達誠老師笑意盈盈,依舊精神矍鑠。

朱達誠,生於1942年,雕塑家。
“你們有什麼安排,我都聽你們的。”老藝術家脾氣溫和,態度更是謙遜,我們建議老師可以在作品前拍一些照片,他笑著照辦,沒有一點架子。
他此次為天趣「破冰2020」展覽準備的繪畫作品直接擺放在工作室裏,我們與朱老師的對談索性就從這批充滿力量的繪畫開始。

朱達誠 美學沉思10
88x90cm
2017
焦墨紙本
這批繪畫作品創作於2017年,彼時有朋友同朱老師閒聊,建議他不如在創作雕塑的閒暇時間嘗試一下繪畫。
“我要畫什麼呢?我想把自己感受最深的東西畫出來。”他始終記得剛來香港的那幾年,“從零開始打拼,剛開始的感覺,那種無助,無奈,壓抑,我始終想有一天,我要把這種感受畫出來。”

朱達誠 美學沉思8
88x90cm
2017
焦墨紙本

朱達誠 美學沉思7
88x90cm
2017
焦墨紙本
朱老師出生於湖北,四十多歲時移民到香港。他用“一個從社會主義社會長大的人,來到資本主義社會從零開始打拼”來形容當時的自己,不會說粵語,生活習慣完全不同,文化和意識形態也相差甚遠。
人至中年,來到陌生的地方一切從頭開始,從開始做設計到後來租下第一間畫室,他用了十多年。“那些無助、無奈,我始終印象太深了。”
於是他把這一切的感受宣洩於紙上。這些仿若素描的焦墨作品用粗獷雄渾的筆力展示著人體肌肉之美,仿佛將雕塑置於紙面之上。

朱達誠 美學沉思6
88x90cm
2017
焦墨紙本
畫面中人體的手腳有一定程度的放大,並不嚴格遵循正常的人體比例。因為他在創作時追求的並不是精確的比例和筆觸,而是情感的渲染和表達。他在畫面中呈現了一種樸拙之感,仿佛斧頭劈下,充滿當頭一棒的震撼——“這是壓力之下產生的張力。”
“雖然有壓抑,但不會壓倒,還是要有力量,要挺起來。”

朱達誠 美學沉思4
88x90cm
2017
焦墨紙本

朱達誠 美學沉思1
88x90cm
2017
焦墨紙本
創作畫面中的男女並不是對具體模特人體的摹畫,而是他表達內心自我的載體。
壓抑之下的迸發,躁動之上的蓬勃,在這間不大的工作室裏,這些人物是如此充滿生命力,似乎要衝出畫面,帶著要衝破逆境的決心和人類全力以赴的意志。
正契合了我們這次群展的主題——“破冰”。

朱達誠 美學沉思2
88x90cm
2017
焦墨紙本

朱達誠 美學沉思5
88x90cm
2017
焦墨紙本
2
我們整理著採訪問題和框架,抬眼一看,朱達誠老師已經在身上加上了一件米色的馬甲。
“做訪問嘛,讓我也穿得好看點。”朱老師笑起來頗有孩童的神采,還從廚房裏拿出茶具給我們泡茶,氣氛更熱絡了起來。
我們很難不注意到他身後的工作室裏堆滿了大小不一的雕塑和模型。朱老師上世紀60年代便入讀湖北藝術學院美術系雕塑專業,受教於張祖武先生,後來更是考入中央美術學院雕塑系研究生班,受教於錢紹武先生,專業功力深厚,甫一進入他的工作空間便能窺知一二。

朱老師工作室中擺滿了大大小小的雕塑
朱老師一邊把玩著手中逼真的《李小龍嫉惡如仇》玻璃鋼小雕塑,一邊拿出創作時的手稿,上面有他為李小龍設計的不同動作以及最後定稿——這是朱老師設計雕塑的最基本流程。我們也知道朱老師要開始和我們聊他的老本行了。
《李小龍嫉惡如仇》雕塑創作時的手稿
這次朱老師即將於天趣展出的小雕塑作品風格顯著,《融》的線條簡練;《天地之舞》和《歸去來兮》則是女媧人首蛇身的再現,只不過前者向上延伸,後者向兩邊舒展,前者用的是頗富歷史積澱的銅,後者則是香氣依稀留存的樟木——這個上古傳說中華夏文明的始祖一直是朱達誠創作的重要靈感來源和反復探討的命題,他也樂於使用不同的媒介和方式呈現。
朱老師即將於天趣展出的小雕塑作品
在他多年的雕塑生涯中,用時最長的莫過於目前立在香港西環孫中山紀念公園的孫中山雕塑。
從2009年開始構思,到2011年最終落成。朱老師從勘察地形、前往湖北的博物館查看孫中山從海外歸國時的照片、將照片上人物的神態動作結合自身理解進行再創造(比如細到手肘上的西服是否應隨風擺動、頭部的轉向等)、再到與美院的學生在大夏天時赤膊上陣鑄造,朱老師還拿出了他在設計過程中做的小模型,我們也仿佛跟著他親歷了整個過程。

當年朱老師與美院的學生在大夏天時赤膊上陣鑄造孫中山像時的留影

孫中山雕塑的大幅照片,也一直陳列在朱老師工作室中。
最初製作這個雕塑的競爭異常激烈,最終朱老師爭到了這個機會。他說,“我想向香港人證明,華人也有這樣的人才,可以做出優秀的雕塑作品。”
過程亦是艱辛的,每一次完成作品都像生了一場大病一樣的朱老師,在完成孫中山雕塑後馬上進了醫院放了心臟支架。而那一年他已經70歲了。
他說:“在香港這個社會,能做幾件對得住自己,對得住香港人的作品,還是蠻好的。”

天趣所拍攝的工作室中的朱老師,時年79歲。
3
朱達誠老師工作室裏的寶貝頗多,他也樂得向我們一一展示,每個作品背後都有一段有趣的故事,或者與一些有趣的人相聯結。
朱老師向我們展示他喜愛的一件小雕塑
朱老師曾經有一段在湖北黃陂開辦學習班,教授秋收農忙後的學員做雕塑的經歷。在當時有限的條件下,他摸索出了一套“短、平、快”的教學模式,把多年積累的雕塑知識提煉濃縮成幾個月就能學會的簡明扼要的教學方法。
後來他培訓出了400多位泥塑者,有些人的作品出現在了中國美術館,有些在雕塑界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績。朱老師談起這些時頗感自豪,他一生可以說是桃李滿天下,“這是一個雕塑藝術家身上的責任與使命”。
朱老師工作室中琳瑯滿目的書籍
我們也不可避免地聊到變化多端的今年,問及2020年疫情期間對於他有什麼特別的影響,“我仍然過著平靜的日子,在工作室裏創作,當然從思考到作品最終成形不是那麼快的事。”他笑了笑,繼續往我們的杯裏倒了茶。
我們與朱老師的訪談幾近三小時,他聊藝術,談人生,言語間處處透露的是豁達。
離開他的工作室後,他說,“好啦,我要回家啦!走路10分鐘就到!”轉身背上一個簡單的書包,逐漸融入了香港華燈初上的街頭。